图书简介
孔海娥博士的《女性生命历程的角色实践——以湖北省燕山村为例》以荆楚之地女性的生命史作为研究对象,她的目的是要解读当代中华大地女性的命运。
也是荆楚之地,也是女性的命运,2000多年以前,离本书所述燕山村并不算太远的地方,有一位女子的名字被流传了下来,她就是闻名遐迩的王昭君。昭君的生命史颇为跌宕,她是西汉南郡秭归宝坪村人,本是一个平常人家的小女孩儿,因为生得眉目姣好,她命中注定要有一番风云际遇。当那个好色的汉元帝刘奭昭告天下遍选美女时,她的命便不由自主了。据《汉书》、《后汉书》以及《西京杂记》等典籍记载,她因在宫中不愿意贿赂画师王延寿而没有被元帝所了解,这么看来,皇帝的地位与权势似乎并没有成为这位女子的爱情基石。于是,昭君又只好听命,她被选择出关去实行国家的和亲政策,嫁给了北方匈奴首领呼和邪单于。等到这个呼和邪单于死了,她“上书求归”,皇帝又命令她遵从“父死,妻其后母”的“胡俗”,她只好忍受极大的委屈,嫁其长子。她与两位匈奴首领的婚姻及感情是好是坏,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出塞事件本身却是胡汉和亲的见证,从此边塞的烽烟熄灭了50年。这些事迹使她成为一位历史名人。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讴歌,其主题大致有二:一为“昭君怨”,如庚信《王昭君》诗云“拭啼辞戚里,回顾望昭阳。镜失菱花影,钗除却月梁。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绿衫承马汗,红袖拂秋霜。别曲真多恨,哀弦须更张”;二为“昭君赞”,如董必武《谒昭君墓》诗云:“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而在我看来,昭君内心的个人意识与家国意识之间的张力关系应该得到揭示,2009年我到了昭君墓前颇有感慨,模拟昭君应答千古诗文的口吻写了一首诗:
我本香溪一山民,
只为家国任生平;
词客年年裁新句,
未识寻常女儿心。
或许认为昭君的例证可以作为博厄斯学派“文化决定论”的证明。博厄斯的弟子本尼迪克特和米德都阐述过这一经典理论。就以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为例,米德发现社会文化决定了性别差别而不是两性的生理特征决定这一差别。在她所选择的三个部落中,阿拉佩什族中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温柔的、女性的、顺从的、没有攻击性,“就像我们期望中的女人们的行为”。蒙杜古马人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冷酷残忍、暴烈而富有攻击性,“则像我们期望中的男人们的行为”。德昌布利族中“男人们的行为像我们传统中的妇女那样——敏捷、卷发、去商店买东西,而女人们则精力旺盛、善于经营、对自己的配偶不盲目崇拜。”在这里,“文化模式”就像一个模坯,人只是柔性的水,流到什么模坯之中,就成为什么样的形状。但是,假如让温柔的、顺从的阿拉佩什女性嫁给德昌布利族那些娇滴滴的、天天摆弄着各种卷发不干活而专事于取悦于女人的男人那里去,她们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她们到底是被原来的“女人似男人”的文化模式决定呢,还是被新的“男人似女人”的文化模式决定呢?米德的研究中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看来,文化决定论似乎还不能解释王昭君一生的命运:如果被胡地文化决定而忘记了她的家国,她不可能有效地执行和亲政策;如果被汉文化决定而不能适应胡俗,她也不可能在胡地生活很多年。
因此,对于因“从夫居”而易地生活的女性的生命历程研究可以使传统研究领域有所拓宽,并使研究主旨有所深化,就此而言,正是本书选题的价值所在。孔海娥博士在本书中认为,女性在孩童时代被她娘家的文化模式塑造。她提出了一个“结构性情感”的概念,这是指女性在娘家生活中习得的关系亲疏以及关系处理模式的一种性情倾向。而当她跨入夫家之门时,这种“结构性情感”进行了她所称的“跨空间运作”。这种运作是解决娘家与夫家文化模式冲突的策略。也正是在这里,她将“实践”的观点引入了研究之中,“运作”就是一种实践。因为实践具有生动性、不定性、情感性、即时性、鲜活性、具体性等特点,文化模式或结构只要进行再生产,总要在实践中进行。当女性与一套完全不同于自己生活模式的另一种模式相碰撞时,原先的模式遇到了新的环境,她们就在实践中主动地慢慢调适。孔海娥运用了皮亚杰的“同化”与“顺应”的概念,来解释这个实践过程。在这种“碰撞”与“并接”的实践中,即在娘家与夫家两种结构模式的冲突与调适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结构模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新的结构模式与原来的结构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孔海娥看到这种娘家的结构性情感在夫家无论多大变化的生活中依然还在,并没有被彻底消除,它在适当的场合就会不时表现出来。例如,尽管随着社会的变革,农村的养育、教育模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年轻的母亲们在角色实践中不得不积极探寻新的模式的同时,而在日常生活中她们对待孩子的模式中仍会有她们的母亲一辈的影响。这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即传统的情感结构在现代文化冲击下的延续。于此,结构变化的时空特征及规律可以被展示出来:结构性情感跨空间与跨时间运作以后出现的新的结构性情感之中,依然重叠与整合着原先的那个最早的部分。这是一种“文化叠合”现象:一个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原先接受的文化模式在时空变换过程中,许多主要部分并不是以消亡和破产为基本特征,而是经过选择、转换与重新解释以后,依然被一层一层地重叠和整合在新的价值观与文化结构之中。这种新旧并存,并不是由于在力量的消长方面,新的暂时还不能消灭旧的,需要在时间的发展中来逐渐完成替代的过程,而是从一开始就实现了新旧文化形态、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理解、协调、包容、让步。
因此,只要将“实践”引入结构的研究之中,对女性命运的研究就会有新的解释,“文化决定论”也因为增加了模式之间的转换而可以有新的内涵。但孔海娥在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止于此,她在关注不同模式(从娘家模式到婆家模式)对女性生命历程的作用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同一文化模式(娘家模式或婆家模式)对不同个性的女性的生命历程的不同作用。“文化决定论”的预设前提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下,被这种模式所创造的个性具有相同的特征;而本书中的例证所表述的问题是:文化模式再生产总是要通过个体的实践来进行,因为个体具有差异性,所以她们在同一文化结构之中其实践的生动性、不定性、情感性等特征的表达也是不相同的,因而女性个体的命运也是不相同的。在这里,传统的“文化模式”理论因没有考虑个性特征而可能被突破。米德虽然也承认“处在同一文化内的个体间差异”,但她将这种差异“完全归因于作用不同的社会条件”。其实这种差异应该归因于先天禀赋,正是由于禀赋的不同使她们在生命历程中的后天机遇面前的实践形态趋异。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将“命”与“运”设定为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并分别代表这两种情况:“命”是女性生活的文化环境、文化模式,它先于作为个体的女性的生命历程;“运”则是一种人生的运程,是一种充满着各种机会的选择,是一种个性实践形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个体把握与改变。《红楼梦》中甄士隐的女儿小英莲元宵节丢失了,多年后辗转嫁给了薛蟠,这是“命”,她自己是不能把握的;而在小英莲变成香菱以后,也住进了大观园,她个体天赋情性而被才子佳人们吟诗作画的兴致激发起来,跟着黛玉学诗,也终于成为一个“准诗人”,她对自己进行了新的塑造,这是“运”。燕山村女性群像给了我们诸多关于女性“命”与“运”关系的启迪,这些例证显示出与经典理论对话方面的价值。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可以使研究更具逻辑上的自洽性。
最后,我想就民族志写作本身作一些思考。孔海娥博士的这部著作大体上可以看做以村庄为写作对象的“家乡民族志”。而对于以村庄为基础的民族志写作,当今已经有了诸多的反思。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能不能这样说:民族志要成为适合于中国研究的学术样式,它必须经过改造。
民族志的形式是现代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费孝通先生曾就人类学的产生发表过如下的意见:在争夺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个怎么更好地统治殖民地的问题。老牌殖民主义者大英帝国带头搞起所谓“间接统治”来了。利用当地原有部落组织和原有统治势力,制造可以依赖的社会支柱,来加强对当地人民的剥削。这是一个很毒辣的反动政策。要实行这个殖民政策,就要搞调查,人类学者就应运而生。
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革命,民族志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新的进展,实验民族志产生。但中国与西方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的”(或称“研究本质”)这三个问题上仍然不同。马尔库塞与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认为,20世纪人类学承诺了“描述异文化”与“反思本文化”两大任务,前一任务基本完成,后一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人类学被他们作为文化批评提出来。然而,当代中国的民族志作品,由于研究对象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异文化的研究,所以其研究目的也并不是作为对本文化的反思与批评。
因此,如果民族志依然是人类学学科的立足基点,如果中国人类学者依然要去进行民族志写作,我们应该充分关注中国民族志的自身特点,只有这样,方能说明中国人类学者对于民族志样式的某种独特思考。中国的民族志作品应该与数千年悠久的文字历史、高度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国家观念相联系,就此而言,也正是本书应该得到加强的地方。
朱炳祥
2012年1月16日于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
作者简介
图书目录
相关推荐
-

图书 中国农村研究.2020年卷.上
作者:徐勇
图书 中国农村研究.2020年卷.上
-
2
图书 男人的声音:16位“性别平等男”讲故事
作者:朱雪琴 方刚
图书 男人的声音:16位“性别平等男”讲故事
-
3
图书 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的福利效应研究
作者:聂建亮
图书 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的福利效应研究
-
4
图书 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回顾、反思与前瞻
作者:张勇
图书 新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回顾、反思与前瞻
-
5
图书 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阈
作者:贺祥林
图书 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阈
-
6
图书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作者:钟涨宝
图书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
7
图书 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理论、案例与实践
作者:詹丽 何伟军 阚如良
图书 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理论、案例与实践
-
8
图书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研究
作者:杨庆毓
图书 大理白族传统婚俗文化变迁研究
-
9
图书 阿拉贡研究
作者:沈志明
图书 阿拉贡研究
-
10
图书 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与形态
作者:王文俐 李诗原
图书 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与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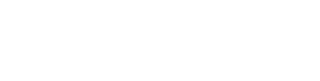
 切换用户
切换用户




 查看图书详细信息
查看图书详细信息
 3,查看图书网页阅读
3,查看图书网页阅读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豆瓣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