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全集
图书简介
《文集》的编者希望我写一篇自序,我只得勉为其难。经反复考虑,我决定在自序中简述一下写出《文集》中各项著作时的社会气氛和我的思想背景。这是我在目前这种精神状态下能够勉力完成的,而且这也可能对读者了解《文集》中各项著作的意义略有助益。
《文集》中所收集的各项著作,除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纯文字上的改正外,都保持了它们发表时的原样。这是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当然,我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感情,却不必也是我今天的思想感情。
(一)
我的学术兴趣,始于中学时期。
1937年春我考入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即第一中学)。我非常喜欢这所学校,它很有一些大学风范。学生思想非常活跃,自学课外知识之风很盛,自学组织很多。我上这所中学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和“七七”抗战之前。生活书店的书籍,对长沙的青年学生颇有吸引力。我读了不少生活书店的“进步书”,从通俗的小册子,到马列原著的译本。后来我又由阅读生活书店的书籍转到阅读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和汉译名著。在读过的商务的书中,我真正理解的实在很少。记得1937年暑假,我从商务买了一本胡仁源翻译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每天下午我用两个小时读这本书。读了大约两周,我还在读它的长序。许多诘屈聱牙的译文,我几乎都能背诵,但却是不知所云。在商务的书中,有两部对我很有影响。一部是刘琦翻译的《逻辑》,原作者是枯雷顿。我现在猜想,大概就是Crighton著的Logic Inductive and Deductive。另一部是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小学时,我读过《论语》、《孟子》、《古文释义》,并且还能背诵。有了这个古文基础,再加上冯先生浅显明晰的解释,我读《中国哲学史》在文字上是没有什么大困难的。当时我就想,等我在大学学习几年以后,我也可以写一本《先秦伦理学史》。我知道冯先生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为了跟冯先生学习中国哲学,我考入了西南联大哲学系。
在联大一年级时,我偶然买得一本旧书,罗素著的Problems of Philosophy(《哲学问题》)。罗素清晰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令我赞叹不已。此书我细读过好几遍。有时我去翠湖散步也带着这本书。在风景如画的湖堤上,找一个僻静的茶座,一壶清茶,两碟南瓜子,一边饮茶,一边细读罗素这本书。陶然自得,境界高绝!
读过罗素这本书后,我才觉得我开始了解哲学为何物。这本书引起了我对西方分析哲学的兴趣,决定了我大学几年学习的方向。我把伦理学,特别是直观性较强的但论证性较差的中国伦理学,暂时搁置一旁。
我读大学时是40年代初期。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如日中天的时期,处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大哲学系,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联大图书馆十分简陋。但Language,Logic and Truth(《语言、逻辑与真理》)、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语言的逻辑语形》)等著作在昆明还是能找到的。由于我当时对分析哲学的浓厚兴趣,我自然对逻辑实证主义也感到浓厚兴趣。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命题(语句)只有两种,一种是分析命题,另一种是综合命题。分析命题的真,是根据语言规则或逻辑规则得出的。综合命题的真,是根据它所指称的客观事物的情况得出的。形而上学的命题(语句)既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综合命题,既不能根据语言规则或逻辑规则得出它的真,也不能根据客观事物的情况得出它的真。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可证实性,因而是无意义的(sinnlos)。
在联大哲学系,大致说来,年轻人比较重视或同情逻辑实证主义,而年长的教师则多数不喜欢或不理会逻辑实证主义。
在联大哲学系,也有一些人为形而上学辩护。他们认为:哲学(形而上学)命题是分析命题;哲学命题是通过逻辑分析法得到的。当时我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人们很难证明哲学命题是分析命题,也很难证明分析命题能起通常所说的哲学命题所起的那种作用。我承认,哲学命题的确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分析命题,也的确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综合命题。我把语句分为两大类。一类我叫做S-语句,另一类我叫做V-语句。S-语句就是科学语句,又可再分为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V-语句就是价值语句(或评价语句)。我认为哲学语句是V-语句。V-语句的确不具有S-语句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但它却具有它特有的意义,也具有它特有的证实方法。因此,我虽然同意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形而上学的某些分析,但我却反对他们关于形而上学的结论。我反对笼统地把形而上学命题说成是无意义的,我也反对取消形而上学。我这个看法,最早可能是受了Ogden和Richards的The Meaning of Meaning(《意义的意义》)这本书的启发,后来又从Morris的Sign,Language and Behavior(《指号、语言与行为》)得到某种支持。
我当时也喜欢说:“高明的哲学,应像数学那样严密,应像诗那样美,应具有宗教那样激励人心的力量。”我这些蒙昧的模糊的思想,是想表明哲学(形而上学)同科学、文学和宗教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二)
1949年春,北京解放。不久,北京就成立了社会科学联合会办事处,地点是东城金钩胡同。办事处组织了三个讨论组,参加人都是北京的学术界人士。其中一个讨论组是逻辑讨论组,这组的召集人是金岳霖先生。我参加了这个组。这个组有十几个人参加。年纪最长的是傅桐,他当时已有约70岁,比金先生还大10岁左右。另外两个组,可能是叫做哲学讨论组和政治经济学讨论组。
逻辑组的开会时间,是每星期天上午9点至12点。逻辑组总是准时开会,出席率也最高。
逻辑组讨论的问题,大致都是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形式逻辑的矛盾律与辩证法”、“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等主题。讨论十分热烈,常常到了散会时间而不能散会。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发人深思,刺激我去找寻正确的答案。这个逻辑讨论组是我一生中最早参加的正式学术活动。
逻辑讨论组的活动进行了约两三年,大约在1952年秋天院系大调整以后解散。
1951年秋,清华大学哲学系招收了解放后的第一班新生,同时也第一次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课程。哲学系决定:由金岳霖先生担任“辩证唯物主义”的课堂讲授,每周四小时;由我主持课堂讨论,每周两小时。
每次课堂讨论之前,我都拟好一个讨论提纲(即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发给学生。我事先也充分考虑:对这些问题有多少可能的回答以及各种回答的优点和缺点。金先生有时也来参加课堂讨论。课堂讨论进行得活泼、热烈、深入,保持了清华哲学系那种喜欢辩论和坚持真理的传统作风。每次课堂讨论,都由我作出总结,表明我对这些讨论问题的看法。
这一年“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使我对“辩证唯物主义”中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系统了解。
解放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根据苏联当时的经验,在教育方面我国进行了高等院校的大调整。1952年秋,我从清华大学调到(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工作。
北大逻辑教研室调集了南北八个大学的逻辑教师,一边进行教师的思想改造,一边进行逻辑课程的改革工作。每周至少开会一次,每次三至四小时。会上对形式逻辑课程的内容展开热烈的讨论。有些人强调形式逻辑课程的改革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也就是必须学习苏联的逻辑教本;另一些人则强调必须遵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传统,也就是必须遵循传统逻辑;还有一些人则倾向于应用数理逻辑的某些观点和精神来处理形式逻辑课程中的问题。我基本上属于上述的第三类人。
为了形式逻辑课程的改革,为了提高我的教学能力,也为了追求知识,我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还必须细读近百年来西方那些有名的传统逻辑教本。
1952年秋,我被派去给北大一年级学生讲授形式逻辑。学生约三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哲学系逻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也去听我讲课,我还作为辅导员参加大一学生形式逻辑课的课堂讨论。
当时北大全校各个学科都在进行课程改革。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就形式逻辑这门大学必修课程来说,我是很赞成这条原则的。我当时认为: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是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实际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因此,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必须结合自然语言授予学生更丰富的逻辑知识,同时也必须在讲课中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这个看法,在我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54年春,我主动请求退出讲课工作(当时上讲台讲课是一种莫大的光荣),而去同王宪钧等几位同事为逻辑教研室草拟逻辑课的教学提纲。以后几年,我有了较多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
当时我有两方面的研究兴趣。一方面是对形式逻辑的哲学问题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对形式逻辑联系实际思维的兴趣。但是,就当时的情况说,争论最激烈的并且最急需解决的,是形式逻辑的哲学问题。因此,我的研究工作就集中在形式逻辑的哲学问题方面。
在当时的北大逻辑教研室,以及当时的中国逻辑学界,概念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我选择了概念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不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说,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理论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苏联当时许多关于概念的说法都来自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笔记》。因此。黑格尔的《逻辑学》也是很重要的。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也花了很多时间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当然我还花了很多时间阅读那些注释和阐述亚里士多德思想和黑格尔思想的文献。
1955年秋,我由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我从1954年到1957年反右以前这几年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三项成果:《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论文)、《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论文草稿)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专著草稿)。
《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连载于1956年的《哲学研究》。这篇论文可归纳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理论,第二部分是黑格尔的概念理论,第三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理论。这三部分都是哲学史性质的工作。但相对来说,第三部分的原始材料是比较少的。这第三部分中,包含了许多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发挥。严格地说,我有时是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应如此说,而不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是如此说。高明的读者应当是能够体会的。
这篇论文是对当时苏联和我国的哲学界和逻辑界的挑战。这篇论文最后一段说:“作者希望:在诸多谬误的灰烬中能杂存着几粒真理的星火,由它们将燃起科学的深入的创造性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我所希望的星火燎原,当然还不是已经实现的存在。这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但这却是一种郑重的批评。
三年困难时期,大约是1962年,北京市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需要有一些论文在会上宣读和讨论。我就把《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草稿改写成正式论文,并油印成册,在会上散发和宣读。又过了大约20年,这篇论文于1981年在《哲学研究》上正式发表。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草稿经过修改,于1965年形成初稿,198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这三项著作,就其发表的日期说,虽先后相隔三十多年,但它们都是1954—1957年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苏联和我国,从二三十年代起,就流行着许多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错误看法,其根源都来自黑格尔的《逻辑》。黑格尔在《逻辑》中本来就说了不少糊涂话。后来某些人又变本加厉地宣传这些糊涂思想。十月革命后,苏联绝大多数哲学家竟把形式逻辑看作反对事物运动变化的形而上学,因而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看作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论。我国也有许多哲学工作者缺乏判断能力,就跟着人云亦云。要纠正和清除这些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错误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和黑格尔的《逻辑》。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思想是形式逻辑的根本原理,黑格尔的《逻辑》则是辩证逻辑的主要经典,而且这两者又是互相牵涉的。
《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这篇论文虽未直接提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但是事实上这篇论文是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为理论依据的。
《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是1956年发表的。这时,我国正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我精神上十分慰快的时期。我在1957年3月为《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作为专著出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此书完稿后不久,适逢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对教条主义曾给以严厉的批判。我国党和政府,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向科学进军的号角,这是人类文化已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里程碑。当兹盛世,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衷心感奋,诚不能以言宣。谨以此书,作为我对这个伟大时代的第一个小小的献礼。”当时我是何等的欢欣鼓舞!何等的意气风发!也何等的幼稚天真!但曾几何时,反右的风暴竟从天而降。紧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整肃运动,一直闹到1960年,全国人民都在饥饿和穷困中挣扎,才不得不叫“运动暂停”。
在这几年的反右运动中,千千万万热爱祖国、关心人民福祉、而且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们,竟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大鸣大放期间,我正埋头整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草稿,才幸免于难。这一切活生生的事实,使我从天真的迷梦中惊醒,决心跳出哲学是非场,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研究中。
在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不加分别地要求一切学术都直接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大洋古和高精尖的学术研究。1959年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提出编写一本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阅读的《逻辑通俗读本》的计划。逻辑室通过了我这个计划。当我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后,又有人提出:这样的通俗书不应由我个人来写,而应由集体撰写。结果这本书由五位同事(包括我)分章来写,我被推为最后统稿人。这本书花了我前后约半年多的时间。
《逻辑通俗读本》写成后,曾征求了一些逻辑同行的意见,也征求了一些工农兵的意见。读者对这本书的反映颇佳。后来日本和蒙古出版了此书的译本。
1958年秋,我和哲学所一部分研究人员去河南七里营“滚泥巴”。“滚泥巴”就是去农村参加田间劳动。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到农村劳动。我这次下乡是领导指派的。劳动了三个月后,回到北京。我利用回北京后的几天休息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发表在1959年的《哲学研究》上。为什么我当时要写这么一篇文章,具体情况已不能记忆。很可能与《逻辑通俗读本》有关。
这篇文章分为四点:(1)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2)从思维实际中来,又回到思维实际中去;(3)结合我国的语法修辞;(4)多讲逻辑谬误。这四点,实际上就是1952年秋至1955年我在北大逻辑教研室时的思想。
在北大进行的形式逻辑课程的改革中,除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外,还特别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形式逻辑。但对后一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把这理解为:在形式逻辑课程中大量讲授辩证唯物论。另一些人(包括我)则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处理形式逻辑课程中的问题。在我这篇文章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普遍原则。它的具体意义就在于形式逻辑应“从思维实际中来,到思维实际中去”,就在于形式逻辑应“结合我国的语法修辞”和“多讲逻辑谬误”。
1960年2月我被下放到山东省曲阜劳动一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时全国农民都在忍受饥饿的折磨,山东又是重灾区。劳动一年之后,我除了经历劳动、饥饿和浮肿的锻炼外,还亲眼看到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一系列政策的恶果,还亲眼看到广大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还亲眼看到许多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和作威作福。
1960年底,我带着几分浮肿和一身疲劳回到北京久别的家。
1961年春节期间,我去上海探亲,住在亲戚家。手边没有专业文献,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写成了《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这篇论文。它后来发表在光明日报1961年5月的哲学副刊上。这篇论文表明我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走上一个新的阶段。这篇论文包含了以下几点:
(1)讲到不同意义的语句。这类似于奥斯汀(J.L.Austin)的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的思想;
(2)明确地提出了语境和具体意义。一个语句的语境,就是这个语句所在的环境,包括时间、地点、说话者、听话者、上下文等。一个语句的具体意义,就是这个语句在语境中的意义;
(3)强调结合语法修辞;
以上两点类似于格莱斯(H.P.Grice)的隐涵(implication)思想。
(4)明确提出要扩大逻辑基本词项,建立新的逻辑系统,即自然语言逻辑。
(1)至(4)的这些思想,主要是我从分析实际思维中得到的。但它们和国外同时期的自然语言逻辑颇有类似之处。
1961年9月,《哲学研究》发表了我的《〈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关于此事的基本情况,我在《怀念金岳霖师》一文中已经作了说明。现在我只想再补充一点:我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气力去反对《论“所以”》的观点,甚至还反对《论“所以”》这篇论文的匆忙发表呢?
在苏联和我国,从20年代起,就有许多人把形式逻辑看作反对事物的运动变化的形而上学,形式逻辑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压制。50年代初,好不容易,形式逻辑才被承认是一门科学,才获得它的生存权。但金先生在《论“所以”》中却提出推理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而且这篇论文中的某些概念又是不够明确的,某些论证又是不够谨严的,这就容易使人认为:既然推理是有阶级性的,那么,研究推理的形式逻辑也是有阶级性的。我在《〈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中提出具体推理与推理形式的分别。具体推理(由于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阶级性)是可以有阶级性的,但是推理形式却是没有阶级性的,研究推理形式的形式逻辑也没有阶级性。
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是形式逻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金先生是我国逻辑学界和哲学界的老前辈。他的学术观点是有很大影响的。为了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也为了维护金先生的名誉,我不得不公开表明我的观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金先生是理解我的。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在金先生的《论“所以”》这篇论文稿发排以前,《哲学研究》编辑部曾委托我对它进行修改。我大约花了两三天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当然我只是从陈述的逻辑性方面进行修改,我没有改动原文的思想和论点。不知此事是否经过《哲学研究》的主编潘老的批准,也不知道金先生是否知道此事。
《〈论“所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发表以后,一个刊物约我写一篇关于推理的文章,并希望我对我国当时关于推理的各种说法进行评论。我没有完全接受这个刊物的意见。结果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阐述亚里士多德推理的逻辑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我根本没有提及我国当时关于推理的各种说法,只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说了两句一般性的批评:“我们不应把亚里士多德奉为神龛中的一尊偶像,我们也不应把他当作阴沟里的一条死狗。”据我现在记忆,我之所以不愿意评论我国当时关于推理的各种说法,主要是因为我不愿意再次涉及金先生的《论“所以”》。由于此文没有满足该刊的要求,该刊把此文推荐给《光明日报》发表。
1961年夏,我被调去编写形式逻辑教科书。
中宣部和高教部在1961年联合成立了文科教材办公室,由大学和科研机关抽调了许多优秀的科教人员,组成了许多教材编写组。每组成员少则几个人,多则一二十人。编写组成员都集中住在颐和园附近的中央党校里,中央党校还为编写组人员办食堂。
形式逻辑编写组共九人,金先生是主编,其他成员都是由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抽调来的。
据说,中宣部和高教部的负责同志,眼看广大科教人员饿得面黄肌瘦,于是想到抽调一部分优秀人员,集中在一个地方编写大学文科教材,尽可能改善他们的伙食,使他们不至于饥饿成疾。这其实就是一种小规模的“抢救措施”。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一部分是各省市在职的领导干部,因而中央党校有时可以从地方政府得到一些额外的物质支援。把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组人员安排在中央党校,就是希望能从中央党校得到一些额外照顾。但当时中央党校自身也十分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组织文科教材编写组,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培养科教人才。编写组成员是老中青三结合,而且还是不同单位的结合。这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有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
形式逻辑教材编写组,每个星期总要开两三次全组讨论会,对教材各章节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讨论也很频繁。这些讨论对所有成员都是有益的,确实起到了培养科教人才的作用。
文科教材办公室曾提出一个编写教材的标准:“提高一寸”。新编写的教材的水平,应当比以前的教材的水平有所提高。假如毫无提高,则编写新教材就失去意义。但全国各高等院校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新编教材要能为大多数高等院校所接受,则新编教材就不能脱离大多数教师的水平。这是教材办公室提出“提高一寸”而不提出“提高一步”的用意所在。
形式逻辑教材的编写,是遵循“提高一寸”这个原则的。因此,《形式逻辑》这本教科书每章每节的水平,并不能代表其作者的学术水平,更不能代表编写组全体成员的学术水平。
《形式逻辑》教科书的初稿1963年完成。1965年,文科教材办公室又让我对全书作了一次修改。我又花了大约半年时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形式逻辑》教科书拖延到1979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我国逻辑教学有相当大的影响。据说,以此书为蓝本所写的形式逻辑教科书竟然有几百种。
从《形式逻辑》教科书完成后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研究模态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疯狂、野蛮、残忍,笼罩着全中国大陆。最初几个月,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整天是学习,讨论,看大字报。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我和许多年长的知识分子就受到审查,进牛棚,参加体力劳动……
197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所有人员都被命令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一边从事体力劳动,一边清查516反革命集团。1972年7月,社科院全体人员又调回北京,继续搞清查运动。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好转。政治学习和其他政治活动明显减少。哲学所的图书室开始开放,也开始重新进口外文图书杂志。从这时起,我恢复了中断将近10年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如饥似渴地阅读外文文献中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资料。
(三)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学术研究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哲学研究的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在学生时代培养起来的哲学兴趣,在压抑了几十年之后,又死灰复燃了。1978年以后,我在学术上又有了两方面的兴趣。自然语言逻辑的兴趣是主流,哲学的兴趣是支流。我把大量时间和主要精力都投入对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但作为休息和调剂,我有时也阅读一些哲学文献,思考一些哲学问题,甚至发表一些哲学的看法。
从1978年起我开始培养研究生。
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全国第一次逻辑讨论会。会前,我家中有人患病,因而没有时间准备论文,也根本没有考虑在会上发言。但当我到会后,逻辑界的朋友们热切希望我作一个报告。我只得在会场上一边听别人发言,一边草拟我的发言提纲。后来我在会上作了约两三个小时的发言,题目是“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全部内容都是讲自然语言逻辑。听众对此很感兴趣。后来,有些对自然语言逻辑感兴趣的人联合起来,成立了“语言逻辑研究学会”。他们经常举办语言逻辑的学术讨论,还写出许多论文和一些专著。
我的这个发言,经整理后,后来发表在1993年《哲学研究》上。
这篇讲话,比《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这篇论文有所前进。它表明,我已从个人摸索的孤立研究前进到与国际的研究合流。这篇发言已显现出我心目中的自然语言逻辑的一个雏形。
《哲学研究》发表的整理稿所依据的资料,只是一位听众的当场笔记和我那份十分潦草又十分简略的发言提纲。因此,整理稿难免有所误漏。但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VI)带有感情色彩的语句(评价语句)”这一节中,出现了许多话。这些话看来确实是我当时讲的。但在20年之后的今天,我却已不能记忆,并且也不能理解了!例如,“‘好者好之,恶者恶之’。‘好者’、‘恶者’是评价语词,‘好之’、‘恶之’是感情语词”。我当时是如何定义和理解“评价语词”和“感情语词”的,我现在已茫然不得其解。
但是,无论如何,语言的感情因素,是语言意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或重要方面。我们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人帮”垮台至1982年这段时间,不仅我自己在努力学习和研究模态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同时我也在哲学所、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介绍和宣传模态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有时我甚至奉劝一些专门研究正统数理逻辑的朋友去研究模态逻辑(自然语言逻辑也是一种非标准的模态逻辑)。因为,我认为,模态逻辑是一块尚未充分开发的处女地,容易产生丰硕的成果。为了自己学习,也为了宣传模态逻辑,我写了一本《模态逻辑引论》。此书在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论A、E、I、O的逻辑意义》、《几种预设》、《介绍C.I.路易斯的意义方式》,是我在这段时间的讲演中的一小部分,它们都是听讲人根据自己的笔记整理而成。
1982年冬,我去美国安娜堡密支安大学作学术访问一年。我结识了好几位年长的哲学教授,也参加了他们的一些学术活动。但我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阅读和收集自然语言逻辑的文献上。我很喜欢安娜堡这座美丽舒适的大学城,我更喜欢密支安大学校园里那种宁静安详的气氛,它使人超脱尘世的扰攘,把全身心都投入艰深的学术研究中。
1983年底,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立即投入上级交下来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逻辑部分的编写工作。我被推定写著“逻辑”这一词条。经过反复考虑,我采取了一个历史观点的写法。我认为,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最能充分而具体地表明这门学科的性质。但也有个别同行不太赞成我这个写法。写“逻辑”这一长词条,花了我不少时间。阅读、审查、讨论和修改别人写的词条,也花了我不少时间。
1986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和清华大学联合举办金岳霖先生逝世一周年和九十诞辰纪念会。会议前约半个月,会议组织者要求我准备在会上作一发言。当时哲学所正在评职称,上下午都开会。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准备发言稿。好在金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我以前仔细读过,并且也听过金先生讲课。我利用晚上和周末的一些时间,在开会的前一天才匆忙准备好发言稿。
这个发言明确断定:就主要内容或整体来说,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的,并且具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因素。我这个看法,与解放后许多对金先生哲学的批判不同,也与金先生的自我批判不同。但我这个看法是严肃认真的,并非为老师文过饰非,并非溢美之词。
在这个发言中,我对金先生解放前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一些批评,特别对金先生解放后的哲学工作也提出了批评。我说:“他高昂的政治热情,影响了他冷静的理智思考。”这句话中“影响了”三个字原为“模糊了”。后来我觉得“模糊了”的贬义太浓,才在最后打印时改过来。
纪念会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了我这个发言,但作了一点删节。后来,1987年《哲学研究》发表了这个发言的全文。
1987年,美国哲学会在旧金山召开年会,邀请我作为特邀发言人在国际组会上发言。会议组织者希望我讲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情况。后来我在会上作了四十分钟的发言,题目是“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变化”。这个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也表明了我对我国哲学界的希望。在发言的最后一段,我表示坚信: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哲学界必会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1957年反右后我第一次在哲学方面的正式表态。这个发言后来发表在美国Philosophy,East and West这个杂志1988年第1期。
1995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金岳霖百年诞辰纪念会。许多老朋友鼓动我再写一篇纪念文章。于是我写了《怀念金岳霖师》一文,发表在《人物》杂志上。这篇文章“表达对老师的怀念,并弘扬老师的美德”。
《金岳霖同志的哲学体系》和《怀念金岳霖师》这两篇文章,一篇阐发老师的哲学,一篇弘扬老师的美德。作为金先生的学生,我写了这样两篇文章,倒是内心感到很安慰的。
1990年秋,我去武汉参加中国逻辑学会的学术会议和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第一届学术奖颁奖大会。会议期间,武汉大学哲学系邀请我去作一次学术讲演。我事先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讲演提纲,题目是“语言、逻辑和哲学”。为了缩短讲演的时间,我临时删去了“语言”这一部分内容。至于我对听众宣布的讲演题目是什么,我已记不清楚。许多听众说,我讲演的题目是“哲学家的使命”。这也很可能,因为我讲演的主要内容确实是哲学家的使命,而且我也一直十分喜欢这个题目。在讲演中,我大致讲了以下内容:
(1)区别正统逻辑与自然语言逻辑。
(2)哲学是非常抽象和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逻辑这一工具,特别是自然语言逻辑这一工具。在这里,我批评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观和哲学观。
(3)强调哲学是世界观,是安身立命的智慧。在这里,我提出了哲学家与哲学匠的区别。
(4)提出哲学是时代的火炬,哲学家的使命是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且对宇宙负责。在这里,我讲到柏拉图在Apolog里所描述的苏格拉底,我讲到康德的名言“在我上者有日月星辰,在我心中有道德规律”。我还讲了《大学》里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我讲张横渠有名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我朗诵这四句话时,突然感情激动,老泪纵横,不能自已。会议主持人以为我身体不适,就立即宣布散会,让我安静休息。
到会的听众,对我这种意外举动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猜测。他们的猜测也可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我自己的直观感觉说,我对历史上那些伟大哲学家的崇高人格无限敬仰。对比之下,我对今天许多哲学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就感到非常失望和惭愧。这种敬仰之心和惭愧之情的交织,震撼了我的心灵。有些爱护我的朋友说:这是我的失态。但我自己则说:这是我流露真情。
我的哲学兴趣,从80年代起就不断高涨。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讲演,虽然是临时的“急就篇”,但也表现出我的哲学思想的主要趋向。我越来越感到伦理学的重要性。我倾向于回到儒家的观点,认为哲学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也越来越感到元哲学的重要性。元哲学以哲学为研究对象。元哲学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哲学的根本性质、功能和使命。这对于我们理解、评价、欣赏和创造哲学系统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今天世界和中国的哲学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些人以艰深文简陋,有些人以糊涂充高明……这就把哲学引向了邪路。我们应维护哲学的可理解性,我们应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哲学应指导人生,促进人生的幸福,哲学应指导社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哲学需要革命或革新。元哲学是推动哲学革命或革新的锐利武器。
80年代后期,中国大百科哲学卷完成了,我也办理了离休手续。我终于盼来了实现我多年梦想的机会——集中全部精力写一本自然语言逻辑的书。这时,我已年近70。为了早日写成这本书,我邀请了我的八位同事和朋友参加这项工作。参加者老中青都有,来自东南西北不同的学术单位。
1989年5月在杭州行政学院,召开了我们这个写作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报告了关于这本书的整个构想以及写作提纲。经过一星期的详细讨论,确定了全书各章节的主要内容、重点和要求,也确定了各章的执笔人。
后来在写作期间,我们又开了几次全体的会议,讨论执笔人提出的各章节的详细提纲。平时我们私下的讨论也很多。
1992年10月,当我正忙着对我写的那几章最后定稿时,太平洋彼岸传来了我老伴瑞芝患重病的消息。这对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只得一面尽快结束写书的最后工作,一面办理去美国的手续。
这本讲自然语言逻辑的书于1992年底完成,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书名是《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从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自然语言和交际在此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我一方面有一种轻松感:多年宿愿,一旦实现,快何如之!但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沉重的心情。我像一个年老体弱的登山者,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攀援之后,仰望前程,离目标还是那么遥远!回顾来路,离出发点又还近在咫尺!好在科学是全人类的永恒的共同的事业,平生不了事,自有后人补。”这是此书刚完稿时我的心情,也是今天我的心情。我相信,自然语言逻辑是一门重要的有辉煌前景的学科,但我们前面也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四)
1992年11月,我匆忙地赶到美国加州山景城家中。惊见瑞芝身体虚弱,颜容憔悴,全失昔日风采,我强为欢笑,但眼泪直往肚内流。从此以后,我就承担起看护病人和操持家务的全部工作。孩子们非常爱妈妈,但他们都远离加州,且工作缠身,只能经常打电话问候妈妈,或利用假日乘飞机来看望妈妈。
我很忙,很累,也很忧伤。孩子们和山景城的亲友,都担心我会被劳累和悲伤压垮。但爱情和道德有伟大的力量,我竟然能坚持下来,直到两年后我的小儿子由北京来到我们身边。
瑞芝患的是骨髓纤维化疾病,目前还是不治之症。患病后期,她转到斯坦福大学医院,得到最好的医疗和护理。但她竟于1994年10月25日溘然长逝。40年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恩爱夫妻,一旦永诀,情何以堪!
瑞芝患病前,我和她曾有一个共同的美丽的梦:等我把《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这本逻辑著作写完以后,我们将在北京或山景城团聚,幸福地安度晚年。她想去美国一所有名的大学,再读一门她喜欢的学科。我则希望能再活15年,重返哲学界,集中精力研究伦理学和元哲学。
但瑞芝不幸去世后,我顿觉一切皆空,万念俱灰。几年来,我虽遵瑞芝临终嘱咐,屡图振作,但收效甚微。尤其近来,我身体日益弱,精力日益衰,记忆和思维能力日益下坠。纵天假我以年,亦难在哲学上有所作为。天也!命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周礼全
1999年3月于美国加州山景城
作者简介
图书目录
相关推荐
-

图书 宋代《周礼》学史
作者:夏微
图书 宋代《周礼》学史
-
2
图书 西周礼乐美学考论
作者:王燚
图书 西周礼乐美学考论
-
3
图书 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
作者:叶修成
图书 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
-
4
图书 二十世纪意义理论的发展与语言逻辑的兴起
作者:陈道德
图书 二十世纪意义理论的发展与语言逻辑的兴起
-
5
图书 汉字文化教育与课程开发体系研究
作者:邵怀领
图书 汉字文化教育与课程开发体系研究
-
6
图书 北宋礼学研究
作者:刘丰
图书 北宋礼学研究
-
7
图书 古史续辨
作者:刘起釪
图书 古史续辨
-
8
图书 箕氏朝鲜史
作者:苗威 刘信君 邴正
图书 箕氏朝鲜史
-
9
图书 復禮堂述學詩:全2册
作者:曹元弼 許超傑 王園園
图书 復禮堂述學詩:全2册
-
10
图书 西周金文礼制研究
作者:黄益飞
图书 西周金文礼制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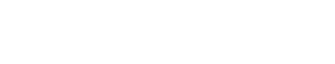
 切换用户
切换用户




 查看图书详细信息
查看图书详细信息
 3,查看图书网页阅读
3,查看图书网页阅读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豆瓣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