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的文艺、审美以及文艺美学的理论研究也在追新趋时中不断变换着风尚、观念和旗帜,有时变换得太过迅速,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文艺界遂有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之感叹,理论研究界的情形也差不太多。变,带来了新鲜和刺激,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和期待,同时也带来了某些不好的风气和倾向。窥之于现实即不难发现,当追新求变成为一种流行的时髦,一种社会评价的标准的时候,也就滋生了一些人的浮躁之气,助长了一种华而不实以致投机取巧的作风和做派,从而对踏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很大的侵扰和伤害,这是学术界不能无视的一种真实现象。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学界并不都是跟风派,浮躁之气尚未将学界的风气全然败坏,许多年来,还是有一些人能够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淡定和“蚂蚁啃骨头”的毅力潜心于重要和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默默地却也是有力地推进着学术理论的研究和思想观念的进步。这其中,有学养高深的老一辈学者,也有英气勃发的中青年后进,聊城大学的谭善明即为后者中的一员。一般来说,文学艺术创作是需要天赋的,学术理论研究也需要天赋。天才人物可以做通才,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各个领域释放自己的创造能量,而一般人能在一个领域或是一个问题上有所成就、有一定的发言权就很不错了,即便如此,还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就像一个农人只有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辛勤地耕耘才能有所收获一样。所以,学贵专一,贵有恒。谭善明2003年以《从话语修辞到认知修辞》的毕业论文在福建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6年以《论转义——话语修辞的一种审美研究》的毕业论文于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到聊城大学任教后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近几年在山东大学做博士后,又以这项课题为基础完成了出站报告。十几年来,他始终如一地进行修辞美学问题的研究,不可谓不专一,不可谓无恒心,这种专一和恒心体现了对修辞研究的痴迷、对学术真理的执著,与同辈人比起来,不能说他多么另类,却委实有点儿与众不同,让人不能不有所看重。他不跟风不玩花样儿,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做着“术业有专攻”的人生努力,可以说是走在正确的学术道路之上。修辞与人类的话语行为和生存实践密不可分。因此之故,修辞研究在西方和东方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分科化不够,修辞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没有形成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在古代只留下一些片段的相关言论,缺乏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和表述。而在西方,虽然修辞研究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不乏系统化的理论研究和表述,却又由于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强大影响,长期以来多是从技巧和手段这样一个很狭隘的角度理解和分析修辞与语言的关系,而未能从人类的话语建构和生存实践层面对修辞的人类学本体属性进行思考,以至于在有的时期还以理性主义的名义贬低和排斥修辞行为。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的修辞研究开始越出语言层面而进入社会实践层面以至哲学层面,从而使修辞研究提升到人类学本体论的高度。受西方学者的启发和影响,中国新时期以来也一改过去只有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修辞问题的传统学术格局,许多文艺美学研究者也开始关注修辞问题,同时理论研究的指向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手法,开始有了更加宏阔的视野和多层面的思考。比如有的中国学者就在总结20世纪文艺美学研究的发展趋向时,在“语言论转向”和“文化学转向”之后又提出所谓“修辞论转向”的看法。应该说,现代以来的这种变化的确使修辞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且由于这种变化也使修辞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中的一种革命性的力量,研究现代学术的学者,对此不可不察。仅仅就此而言,谭善明对修辞问题的研究便是很有意义的。当然,选择一个有意义的课题和领域,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还只是找对了方向,并不意味着自然就会取得成果获得成功,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独特发现和深思的问题及切入路径,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你根本就看不见路、找不到路,通达罗马云云只能成为想象和空话。许多志大才疏者面对学术课题窥其门而不得入,原因概在如此。可喜的是,作为一个年轻学者,谭善明是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切入路径的。在本书中,谭善明明确指出,修辞是以形象的语言来进行说服或实现特定的目的,所以修辞性的语言不同于普通表达的语言,它们虽然同样服务于人类实践,但修辞因其审美特性而增强了表达的效果。特别是当修辞转入书面语以后,它所特有的“美的表达”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语词技巧上的修饰只是修辞活动很小的一部分,修辞的活力表现在它对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活力正是修辞学从它的古希腊罗马传统一直继承下来,并在今天西方得以发扬光大的东西。事实上,这种修辞的活力正是修辞的审美特性的体现。不过,由于修辞本身所无法割舍的目的性,致使修辞的审美研究难以独立,西方古典修辞学是与政治学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当代修辞理论更多从语言层面、社会实践层面、哲学层面三个层面展开,审美研究往往穿插其中但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层面。这就是他所发现的问题所在。基于这一问题意识,谭善明没有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落在讨论修辞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状况,而是聚焦到自尼采以来的现代性修辞观念如何影响了当代思想形态上来。他认为这种现代性修辞观念超越了“修辞手段”、“修辞技巧”的层面,而从认知的层面强调修辞在建构语言、知识、思维以及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而将其定位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它的核心集中于话语修辞活动的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的张力、话语形式变革与认知内容颠覆的合谋。修辞的审美过程以“陌生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感官,从形式上为新观念开辟道路;意识形态过程则表现为话语权力的争夺,是以“新的”思想观念取代“旧的”思想观念。审美过程与意识形态过程既不完全对立,也不完全重合,两者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和斗争,并且不断地从一极走向另一极。20世纪西方文论发扬了尼采的修辞学传统,特别强调修辞本身强大的形式冲动,关注修辞的审美过程在颠覆传统观念过程中的作用,从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到耶鲁学派,一脉相承、层层递进地勾画出一个“转义”修辞的文化景观。可以说,该著彰显审美特性在现代修辞观念中的人类学蕴涵,在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中梳理20世纪西方修辞研究的学术流变和思想冲撞,不仅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也使读者对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的内在思想肌理和文化冲突有了一个更为深刻、明晰的观察、透视和理解。德国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指出,在所有的人类文化活动中都可以发现一种基本的两极性:“我们可以说它是稳定化和进化之间的一种张力,它是坚持固定不变的生活形式的倾向和打破这种僵化格式的倾向之间的一种张力。人被分裂成这两种倾向,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另一种则努力要产生新形式。在传统与改革、复制力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总体而言,谭善明也是从这种二元性或两极性看待修辞活动中的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过程的。他将审美界定为人类感性层面上的一种情感活动,审美在修辞中主要表现为在话语中进行的形式创造,审美冲动使得话语始终保持新鲜活力,并不断推陈出新,保障了话语的生成。他对意识形态的使用则是广义上的,不仅仅指那种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的社会意识,更主要的是指某种固化的虚假观念。不过,他没有简单地从完全对立的角度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认为审美与意识形态在修辞活动中辩证地相互依存、相互生成,有交叉又有斗争,有交叠重合又有相向转化。在审美过程中修辞满怀信心地编织语言的花环,为某种意见进行充满形象的、饱含激情的“强论证”,而当这一论证得以完成,意见也被人们广为认同之后,修辞就从审美滑向了意识形态。不过,修辞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帮凶,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破坏者,从审美走向意识形态只是修辞活动的一半,从意识形态重返审美也是任何话语不可逃避的命运。因为话语在以审美的方式为自己进行“强论证”的时候,必然要化解已有的意识形态(已完成的“强论证”),而当这一任务完成之时,话语并不会停止生成的脚步,又要进行下一次的“强论证”。这样一来,修辞就是既作为一种解构性同时又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整合于自身之中的。修辞带来全新的审美幻象,人们在虚构中体验到审美的快乐,但是审美滑向认知又吞噬这种快乐,同时话语修辞又以转义的方式用审美的力量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这又使快乐得以延续。审美与意识形态就这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这种认识,比起许多西方和国内学者只是简单地把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试图以审美来超越意识形态、打破现存意识形态统治的审美乌托邦理论更为符合修辞话语行为的历史实际,是本书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创新之处。当然,本书还有许多值得重视的优点,相信聪明的善于思考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和总结,这里就不再一一胪列了。同时,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介入修辞研究的学者政治立场不同,思想倾向有别,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也互有差异,因此现代修辞理论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场域,仅仅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这一个问题框架中不见得能把所有修辞研究的头绪、背景和种种纠缠不休的问题梳理清楚、分析透彻。此外,把意识形态只是界定为固化的虚假意识固然有助于建构审美与意识形态二元分离的分析性问题框架,有助于彰显审美在话语构成和人的生命活动中的积极生成力量,但意识形态是否仅仅是固化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在话语构成和人的生命活动中是否只是一种保守的、消极性的力量?这恐怕也还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期待善明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对此类问题能有所自觉和思考,以使自己的修辞美学研究理论预设更经得起推敲,问题论域更具有包容性,言说内容也更为丰厚、更具逻辑说服力。相信他具有这种学术潜力和能力。是为序。谭好哲2012年11月16日于济南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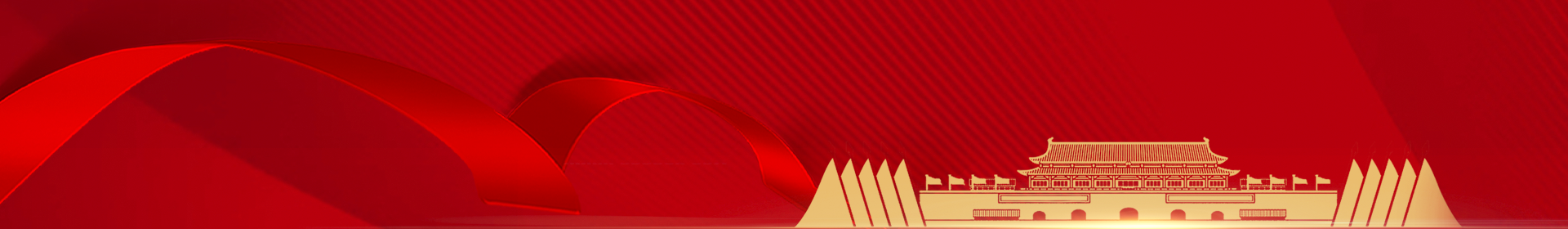

 试读
试读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