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相信每一位有所成就的学问人都渴望出版个人文集,本人亦不例外。但于我个人而言,出版这本文集踌躇颇多。这是因为:第一,37年的专心治学,虽无多少力作可言,但连篇累牍、长长短短的文章细算之下竟累积二百多篇,其中本人觉得颇下些功夫又可以拿出手的文章、专论也多达一百多。而这一百多篇中光是二万、三万乃至五万字数的长论文竟也有十篇左右,要在总字数多达二百多万字的文章、论文中精选由赞助出版单位给定的30万字,应当是一件很容易的也很愉悦的事。然而,由于我个人人性中的弱点在这次选编文集过程中再次显露,使本来很容易的事变得很难,而原本是一件很愉悦之事变得很纠结。首先,要在二百多篇文章和专论、总字数达二百多万中选出14篇合计30万字的专论,就要直接面对大量的文稿由于不能入选而被迫放弃。“敝帚”尚且“自珍”,此乃人之常情,更何况自己舍弃的是花了37年的心血苦心钻研的学术成果,不忍之心难于言表。其次,本人原计划出版个人《全集》,且已经付诸编辑。但出版个人《全集》也是难下决心,一者是个人目前正处在第三次学术生命的巅峰时期,研究欲望强烈,新的选题迭出,欲罢不能。近十年来,每年五至七篇专论总是能发表的,两至三年出版一本专著也成为常态。现在就出个人《全集》,若干年后,势必要出个人《续集》或《补集》,作为有些偏执的理想主义者的本人,更希盼出版一部个人完整的《全集》。二者个人现在出版个人《全集》,由于获得出版资助显然无望,所以也面临很大的出版所必须面对的资金压力,此乃“欲上不能”,纠结的心境同样难于言表。这种纠结的心态困扰我几年之久,直到最近才最终作出决断:先集结自己认为最有代表性的重量级专论,以文集的形式先行出版。
关于这本文集,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一)论文的遴选本着如下一些思路:
第一,只选精的,不选一般的。坦率地说,本人的全部论文以及著作,并非全是精品,但自我体认还是有些精品,这次遴选的论文都是自我认定的精品。至于一般性的文章、论文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为宣传当时的“新宪法”,即现行的一九八二年宪法所写的释义性的短文,主要是为适应当时向广大公众宣传“新宪法”的需要,自觉学术品性不高,但也自视有一定的价值。对这部分文章待日后有机会出版个人《全集》的时候,再酌情考虑有选择性地收编一些,那些毕竟为我的学术生涯留下的足迹,已经历史地成为我全部学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只选长的,不选短的。由于文集字数的限制,所以精选本人全部文论中一部分较长的论文集结出版。本人治学一向秉持立意创新、打造精品力作的精神,务使自己要做到细推物理、探幽钩玄。本人在写作中一贯拒斥下武断的定义之类的断语。对于我个人来说,诸如“违宪就是违反宪法”之类的话语是绝然不可以接受和说出的,因为我认为这类话语不仅是同义反复,也丝毫不能增加学术品位,更不能引发任何学术兴趣。为此,本人一向认为上乘的学术论文是一定要有一定的体量来保障的,论文是说理而非简单地说事,一定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论则已,一论就要说深论透,让读者明白其中的道理,尽管读者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常见一些论文所提出的问题比其能说明的问题还要多,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败笔,至少不是上乘之作。当然,上述治学精神和写作态度只是个人的体认,事实上是否真的做到了,则需另说。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的长与短只是个人的认定,具有很强的个人随意性。一般说来,以一万汉字为基准,少于万字的,在我的学术层面上就被视为“短文”,而长于万字的,则将其视为“长文”。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绝非一个严谨的认定。在本人的学术文论中,少于万字的,自然是多数;但长于万字的,也不在少数,还有几篇在3万、5万、8万、12万字乃至一篇最长的专论竟达16万字。在此次选编的论文中,一般是选用1—3万字的“长文”,其实只是取其中等的长度。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各篇文章体量大体相等,看起来比较整齐划一,因为人们通常将“七长八短”视为不规则、不协调的体现。现在这样,使整个文集看起来较为整齐和协调。需要再重申一下的是,这种选编的思路主要关注的是其形状,取其学术之“体美”之底蕴是也。
第三,只选宪法学专业的,不选非本专业的。本人治学既不抱定“述而不作”,也不秉持终老一生的“一文主义”,认为那些都是学术大家或一代宗师们才能做的。本人只是普通的学问人,虽说入道37年都坚守自己的宪法学专业,但宪法学博大精深的理论构成都也需要其他众多学科的理论支持或补益,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等,更不待说法学中的各个学科了,特别是其中的法哲学和法理学。基于深入宪法学研究的需要,本人的学术研究涉猎的范围较广,其中包括法哲学和法理学、人权理论、政治学、人类学,等等。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的表现,实属对宪法学研究的助益、拓展或建立交叉学科的需要,其中有些论文也是个人着力打造出来的。但此次选编的专论中还是以宪法学为主。无庸讳言,出版的个人文集希望更彰显个人在宪法学专业的成就和造诣,而不是一个博而不精的“杂家”。
第四,只选多学术层面的,不选单一的。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主题和话语,学者们的研究紧扣时代主题和话语,也是具有社会责任的体现。只不过有些学者对此的理解和把握显得过于偏颇,从而丧失了科学品位上的独立自主性。此其一,再有就是学者个人的研究领域和兴趣也是一个由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或形而上或形而下、或理论或实践、或历史或现实、或超前或未来,等等,全凭个人学术旨趣来选择。本人在学术领域和兴趣上并不“从一而终”,在宪法学专业的范围内涉猎面广,这次选择论文,尽量照顾个人这种研究旨趣,尽量多收一些多层面的论文。一为彰显个人学术研究的特点,二是为满足读者多层次学术好奇心。
第五,只选有代表性的,不选重合的。为了说清说透某种理论或观点,同一主题有时会在不同的场合或以不同形制的文章、专论在各种不同的期刊、杂志上发表,这是学术界常见的一种现象,本人就存在这种现象,像宪法监督、反腐败、反酷刑、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法律监督的价值与功能、检察权的定性与检察机关的定位等论题,就曾以各种形制在各种不同的期刊、杂志上发表,甚至还集结成为专著出版。在此次选编论文集时就面临一个选哪一篇的问题。好在本人自信待选的同一主题的期刊文章、杂志论文中总有一篇能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个人的学术理论或观点,换句话说,就是最具有代表性。此等论文当然是作为首选。读者将在这本文集中见到的15篇论文,可以说都是最能代表本人学术观点的论文。
第六,只选各个时期的,不选同一时期。如果像通常每十年为一个时期划分纪元单元的话,在本人37年不间断的学术生涯中,差不多经历了四个时代,其中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这三个完整的十年代。就个人学术成果而言,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最丰硕,其中可选编的论文自然相对多一些。但考虑到为了全面反映本人的学术研究历程,并作为历史和时代的记忆,所选论文跨越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各个时期,而没有只在最近十几年我个人更觉得满意的几十篇论文中选取。凭实而论,心中颇感遗憾。不过,此等缺憾只好留待日后找机会再弥补了。
(二)《宪法起信论》书名的选定及说明
本文集最初选定《宪法文定》作为书名。鉴于《文定》作为文集的书名在当代鲜有所见,故需要予以说明。
有必要先交代书名的来历。“文定”的书名在现代特别是当代几乎被学术界遗忘了。“文定”,原意为“经过删除选定的文集”。据史料称: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诗人黄宗羲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对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造诣颇深,尤长史学,并开创了浙东学派。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他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集》,又删订为《南雷文定》、《南雷文约》。清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集》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清初诗人靳治荆曾任安徽歙县知县,对黄宗羲甚为仰慕,自谦晚学后进,任内与黄宗羲互有诗文往还。在黄宗羲重新刊刻《南雷文定》时,由靳治荆作《〈南雷文定〉序》以报。其中言道:“(先生)于是尽汰其等身之著,而约存若干首,汇为一编,名曰‘文定’。”从中可以推出,“文定”者含有两层意思,一为“文集”或“诗集”,二为是经过“删除选定”的。
至于本人何以要选定“文定”作为自己的文集的书名,既是偶然,也是情境使然,更是应然。
说偶然,是因为自己在偶然的情况下发见有此书名,那是在2005年本人在浙江宁波大学讲学时,在广阔的校园内有条“浙东学派路”(记得不准确),该路两边每间隔几十米就有一石碑刻文分别介绍明末清初浙东学派各大家的简历及著述。就是在那条路上我发见在黄宗羲的碑文介绍上赫然刻记《南雷文定》的书名。当时就给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一直念念不忘,并立下夙愿,日后自己出文集就以“文定”为名。
说情境使然,是因为自己有一种强烈的“为尊者讳”的内心认同。由于自青少年时期读书起,就熟知、精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革命伟人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的《全集》、《选集》、《文选》,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了一种莫名的强烈印象,似乎只有那些高山仰止的思想家、革命领袖和鸿儒巨擘才有资格出以此书名而编辑的《全集》或《选集》,而这种编辑又不是个人随意而为,多为国家官方权威的学术机构才有资格从事这类编辑工作。至于常人,至少在先前时代极少见到有出个人,特别是由本人编辑并出版《全集》或《文集》的。当然,这只是历史既存状况给自己留下的印象,绝不是也不应当就认定出《全集》或《文集》就是经典作家、伟人和文化名人们的专利。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文化名人包括一些准文化名人们都纷纷出版了个人的《全集》、《选集》或《文选》等,这就证明了上述的“为尊者讳”完全是不必要的,也不符合时代的开放和平等的原则和精神。不过,也常常见诸坊间以《某某自选集》的书名出版个人的文集,我猜想,用一个《自选集》的书名,除了表明是自己编辑成书的过程以外,或许还有一些上述的“为尊者讳”方面的考量也未可知。无论怎样,本人直到眼下还没有勇气冲破本人为自己设下的“禁忌”牢笼,至今还是极不情愿地为自己编辑的文集取名《文集》或《自选集》。
所谓出于“应然”的另一个理由,就是由黄宗羲先生选用所用《南雷文定》的书名(是否是“第一次”使用我不敢确定)所含的成书本意,就是要有“经过删除选定”的编辑程序。前面引用靳治荆先生《〈南雷文定〉序》中所言:“尽汰其等身之著,而约存若干首,汇为一编。”总之要有删除之后的选定这个程序。从这个先人约定的前提条件上看,本人这部文集从两方面满足了这个条件,一是被动无奈的,在37年的学术生涯中,作为做人“另类”的一个应付出的代价,就是居无定所,成了一个处于权威范围之外的“边缘人”,在那个由单位分配住房的年代谁会在意你是否安居的问题。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都是以单位储物间、楼道的角落和办公室的一角为全家的安身立命和治学之所,所受不便、干扰不说,就是无处存放书籍、文稿之类的东西,又在出国进修、讲学期间的几经变换,原来四处保留的一些文稿、书籍和文字资料又大半遗失了;加之自己正处在人生低谷阶段,绝想不到日后还能苟延至出版个人文集的人生和治学结局,所以对个人的文稿等资料并没有进行精心保存,只是个人还有很强的敝帚自珍的惜物之心,所以总算保留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且大部分重复文稿经由发表所以还是保留下来了。这就是遗失后幸存下来的文稿。
二是自己删除的部分文稿。因为并不是全集,所以删除一些在内容上不很重要的文稿,尽量编辑一部分本人认为重要的文稿,当是在情理之中,相信所有他编或自编文集的学人都会这么做的。此外,客观上造成删除部分文稿的原因,就是出版社的要求,不论是出于成书的品质要求,还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后面捣鼓,总之作者只能遵从,即使是极不情愿地顺从,也必须照办。所以最终就是“经过删除选定的文集”,又是宪法专业,是为“宪法文定”。这就是书名的来历。
然而为书起名之事并未到此结束。此书稿在荣获得“老年科研基金评审委员会”批准资助的同时,也提出更改书名的要求。我虽然不清楚是何原因,但相信该委员会的专家们肯定是出于多方面的利好考虑,也体现了对老年科研基金使用的负责精神,当然也包括对著者本人的学术惠顾。于是我稍有迟疑后便立即奉命重新思考为书稿起名的问题。
巧逢三个学术机缘会聚在一起,又促成了新的书名——《宪法起信论》——的拟成。
先说第一个学术机缘。社会学家艾尔·巴比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的基本的、有用的目的,即探索、描述和解释。对于任何一项严肃的社科研究成果来讲,这都应当是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否则就难称得上是符合科学规范性要求的成果。但如果我们还要把思路延展下去,这三项标准似乎并不能使我们得到学术满足,还有研究的目的,所要达到的研究目标及其旨归,更需要研究者加以关注。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目前正大力倡导的“问题意识”。目前中国社科学术界的研究的现状,即使不是普遍,至少有相当高的比例的研究论文、专著缺乏问题意识,尤其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有些著述或许在探索、描述和解释方面很见长,但细察之下,并没有使读者深切地了解这种探索、描述和解释究竟为了什么?究竟要达到什么研究目的?是要解决一个或一些理论上的难点,还是为了破解实践上的一个困局?抑或兼而有之?正是在这一最终的旨归上,分出了有关著述的品位高下。
就笔者个人而言,在长达40年宪法学研究的历练中,逐步体悟到上述“问题意识”的重要,并在创作中践行这种研究理念。读者或许不难从本文定收集的每一篇文论中体悟到经探索、描述和解释或隐或显蕴含的研究旨归。长期以来,笔者个人都是在踌躇满志的研究状态下沿着这条研究进路蹒跚而行的,并以此获得极大的学术心理满足,乃至对这种研究状态及其成果甚为享受。然而,这却导致了对宪法学研究的专业性与中国现实宪法知识的普及性的相互关系出现了一些误判,以致在中国无论在社会层面、政治层面乃至法学专业层面均存在宪法专业知识普及性的严重缺失状态,在很长时期内浑然不觉。这种学术思路和历程的确值得认真地加以反思。
造成上述误判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在主观原因方面:
一是误以为在1982年宪法制定前后,特别是在该部宪法颁行后的三五年间,学术界特别是宪法学术界的集体努力,坊间也协力在出版、发行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新宪法”的内容和精神、原则得到很高程度的普及,一时间,“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法律话语。因此误以为在中国社会各方面宪法知识普及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事实证明,这种对宪法普及情势的判断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第二个机缘是对宪法学的专业性也存在盲目性的误判。以为在现时的法学教育专业化、体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教育体制内,每个有志于法学专业学习的学子们必定受到了良好的宪法专业知识的教育,至于非宪法学专业的部门法学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特别是其中成了名的学者,更是应当具有程度相当高的宪法专业知识的素质。然而,就在几年前围绕有关在制定的部门法中是否应当写上“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引言问题展开的学术大讨论,犹如一声炸雷震醒了我辈“梦中人”。原来在对“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地位”这个举世公认的宪法学入门知识,竟被法学界一些成名的学者所难以理解和接受。本来,要不要写上“依据宪法制定本法”,只是一个有关立法技术问题。写与不写均在两可之间,但是,即使不写,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也是不能被动摇的,制定的部门法无论其法律地位多高,多重要,都不能违背宪法的原则和内容规范。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底线级学术问题,竟在中国法学界引发一场风生水起的辩论,真是令人唏嘘!
然而,有关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和法律地位问题的异见在2013年5月,又以极端的高调再次唱响中国学术界的天空。其主唱的主力军是几位非法学更非宪法学专业的其他学科的学者。他们以“闯入者”的姿态在宪法学阵地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大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只不过这一次并非直接针对宪法的权威和地位,而是拿“宪政”说事,论者在对“宪政”拼尽全力“起信险肤”(《尚书》语)的同时,也将一盆盆脏水劈头盖脸般地泼向“宪政”。本来,“宪政”就是中国语境下对西语的“constitutionalism”的转译的结果,学术界约定俗成,其实完全可以用“宪制”、“立宪政体”、“民主政治”、“宪法体制”等词语代而用之。在中国能否用“宪政”一词以及能否实施“宪政”,本来可以在学术层面进行平等交流和讨论,以达成共识供政治层面考量看是否纳入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中去。然而,有关的学者并不想这么做,而他们那样做的结果除了扰乱视听、误导舆论、干扰正常的宪法学术研究秩序以外,正如一位宪法学权威学者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他们攻击的目标实际上正是中国现行宪法。
以上围绕中国宪法和宪政展现的负性学术动向,可以用“不信”这个词语的意蕴加以涵括。“不信”者,“不相信之谓也”。如何面对和摆脱中国法治和法学术星空中弥漫的对宪法的无识、漠视、轻视乃至反对的这一困厄局面,应当是宪法学界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每个有志于弘扬宪法的学人都应当勇敢地作出这个责任担当。
第三个是机缘是笔者本人还算较早地认识到中国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对宪法“不信”的困顿状态,于2012年写了《宪法文化的启蒙》一文,反复强调对宪法应予相信和尊重的种种理由。该文发表后受到法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说明法学术界对此学术困顿状态有同感。以后,我又相继发表了《宪法文化的自觉》和《宪法文化的超越》两篇论文。但总觉得对于“信”的起始意义来说显得有些超前。为此,原计划中有关宪法文化的系列文章中的其他各篇,于迟疑之中未予跟进动笔。原因之一就在于计划中的专论对于“起信”宪法的底蕴来说,似乎有过于“奢侈”之嫌。时至今日,一个“起信”宪法的念头如系绳之卵始终悬挂在本人的学术心头。
以上三个机缘巧遇而合,在笔者的宪法学研究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有关“宪法起信”的意念,这种意念历久弥坚,总有一种以适当方式表达出来的学术冲动。正当此时,恰似应了中国传之历久弥新的诗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理意境,一个不期而遇的良机突兀地来到我面前,“老年科研基金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们坚持改变原书名的要求,恰似天赐良机。细审之下,在我经心选编的全部文论中,贯穿背后的一条连续不断的红线,不正是让读者相信宪法、信赖宪法、依靠宪法,进而达到尊重和遵行宪法以至将来信仰宪法这样的意念吗?一想到此,现在的书名犹如一道力闪,突然照亮了笔者的学术心田。《宪法起信论》的书名即刻如钉子一般铁钉下来,与此同时,始终悬着的学术之“卵”也稳稳地落在了笔者的学术心间。
然而,如果思虑到此为止,也只能视为守住了宪法学研究的学术底线。不难设想,一部严肃的宪法学术作品只让人“相信宪法”就能得到学术满足了。从学理的层面上看,还应当也必须在宪法理论上狠下功夫,进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更至显微阐幽、极深研几的研究。只有这样,方显宪法学精研的学术本色。在这方面,笔者不仅深有体悟,而且在自己的全部宪法学研究的生涯中始终勉力践行。本文集收录的各篇专论不论效果如何,但总能证明我在这方面追求的良苦用心。如果是这样,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的书名能涵括这类精深的宪法理念吗?我的回答是能。不仅能,而且极恰当地体现了我在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义理的苦苦探索以及孜孜以求。
答案就在“信”的意解上。“信”字古训有多义,“相信”只是其一。“信”另有一义通“伸”,即有“伸展”、“延伸”之意。《易经·系辞下传》有“屈信相感”和“尺蠖之屈,以求信也”的彖文,即是此意之用。《尚书·盘庚上》亦有言:“起信险肤”,即“伸说危险和肤浅”,也用其“伸”之训意。此外,佛学经典《大乘起信论》中有释家阐释的三种“发心”,其一是“信成发心”,即得信成就而发其心,就是起始于“相信”;“发心”之二是“解行发心”,即真如法中深解现前所修离相,以知法性体而发心,即用“伸”意或“微密纤察”的意义;至于“发心”之三是“证发心”,即以依转识说为境界,而此得证者无有境界而发心,更是在“伸”意或“微显阐幽”的意义上而使用的。(详见王建光文:《菩提之心的“发起”与“守护”》,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7日)
如此说来,《宪法起信论》的书名不仅涵盖了为宪法争“信”的创作初衷,更蕴含了笔者在近40年宪法研究中对宪法精义及其伟大实践真谛的极深研几的追求。两相得而宜彰,一切尽蕴含在《宪法起信论》的书名之中。古人云:“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此真然也!
为一个书名竟费了如此多的笔墨,无非是借“名”发挥罢了,终归还是让读者相信宪法,信赖宪法,还要深深地理解宪法,更不要忘记的是,努力践行宪法。
以上可能只是笔者个人的粗鄙之见,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不仅“起信”而且“重信”,乃至“深信不疑”。
是为自序。
作者于北京寓所半步斋书房
2015年3月26日
作者简介
图书目录
相关推荐
-

图书 中国宪法类编
作者:陈荷夫
图书 中国宪法类编
-
2
图书 宪法学专题研究
作者:陈焱光
图书 宪法学专题研究
-
3
图书 宪法学的新发展
作者:莫纪宏 翟国强
图书 宪法学的新发展
-
4
图书 反思型宪法观导论
作者:程关松
图书 反思型宪法观导论
-
5
图书 宪法学原理
作者:莫纪宏
图书 宪法学原理
-
6
图书 独联体国家宪法比较研究
作者:任允正 于洪君
图书 独联体国家宪法比较研究
-
7
图书 宪法权利实施研究
作者:朱全宝
图书 宪法权利实施研究
-
8
图书 权利话语的生长与宪法变迁
作者:张烁
图书 权利话语的生长与宪法变迁
-
9
图书 中亚国家宪法变迁研究
作者:董和平
图书 中亚国家宪法变迁研究
-
10
图书 通货膨胀的货币宪法规制
作者:鲁勇睿
图书 通货膨胀的货币宪法规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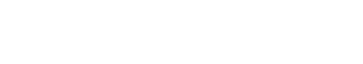
 切换用户
切换用户




 查看图书详细信息
查看图书详细信息
 3,查看图书网页阅读
3,查看图书网页阅读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豆瓣评论